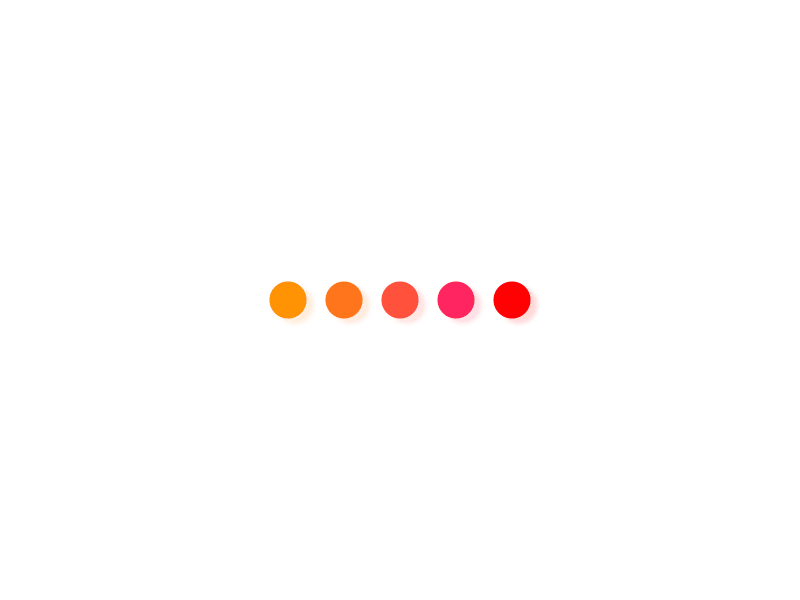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需要,在路径、形式、内容、对象和目标等诸多层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本文聚焦“翻译之为用的实际评价”“中国话语的译介原则与方法”和“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通过观察提出问题,期待学界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展开相应的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翻译价值;中国话语;译介原则;文学翻译;语言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一词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许钧、刘云虹,2016: 100)。我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需要,在路径、形式、内容、对象和目标等诸多层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我们翻译学界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进行思考与探索。基于本人对翻译活动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
1、翻译之为用的实际评价问题
关于翻译,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是翻译之为用的评价。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似乎有个现成的答案,就是季羡林先生谈翻译之为用的那段话,他以中华文华的发展为例,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灵应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2001: 3)把翻译的作用提高到中华文化永葆青春的“万灵应药”的高度来认识,应该说已经很到位了。我对季羡林先生的这段话,十分认同,在多篇文章中引用过。可是作为一位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的教师,我经常听到同行们抱怨,说翻译成果在高校教师职称评价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很多单位甚至根本不把翻译当作学术成果。实际上,我们如果再把目光投向社会,我们会发现,对翻译价值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工具性的层面,翻译不可缺,但是很“廉价”。如果说在高校,翻译往往被认为“无用”,“不算成果”,深深地挫伤了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在翻译师资队伍建设与翻译人才培养方面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上,翻译的廉价,则往往造成翻译不被重视,似乎谁都可以做翻译,翻译的质量得不到切实保证,翻译的作用因此而大打折扣。这些问题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
首先是翻译之用评价的工具性与功利化。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各界,往往是在实用的层面去考量翻译的作用。这样的一种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大的改变,有两种情况尤其值得重视:一是随着语言服务行业的兴起,翻译被定位于语言服务的范畴,这种定位容易将翻译的作用归结于其工具性。二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刘云虹,2015: 3)。工具性与功利性这两种情况应该引起翻译学界的高度警觉,因为前一种情况把翻译的作用定位于实用层面,归结于工具性,必然导致矮化翻译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缺乏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近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来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翻译学界缺乏翻译价值观的指导,过分强调翻译活动的实践功能,在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的讨论中,片面强调以所谓的实际效果为准绳,忽视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深刻认识。
其次是学术界轻视或忽视翻译价值。高校职称评审中不把翻译成果作为教师研究成果,这一现象很普遍。针对这一现象,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国翻译》杂志2017年第2期上。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在实际的层面,为翻译成果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的认定提供某种参照,二是在理论的层面,希望引起翻译学术界对翻译价值进行进一步思考与探索。很遗憾,这篇文章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翻译学界对文章所涉及的有关翻译价值的探讨没有足够的呼应。
实际上,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我们外语学科,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也还远远没有到位。我可以举两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是学术译著的作用被明显矮化。学界有重研究、轻翻译的倾向。一个学者,花了多年时间的钻研,费尽心血翻译了一本很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很多高校不被计入学术成果,可有的学者根据这部学术译著,作了一点介绍与肤浅的阐释,标之为论文,便被堂而皇之地视为研究成果。这种现象很普遍,但没有引起我们翻译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很不正常的。二是学术译著被明显侵权。我们现在都特别强调学术规范,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文字,都必须交代出处,不然就会视为抄袭,至少是学术不规范。在这一方面,我也做了一些观察,发现学术界对学术著作与学术译著明显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对学术著作的引用,注释比较规范,但对学术译著的引用,往往只注明作者,而根本不提译者。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侵权。我们翻译学术界,对翻译主体有深入的研究,但在学术成果的引用上,翻译主体被忽视、被侵权,我们却视而不见。这种现象前些年很严重,这几年有了比较多的改善。
就学术影响的具体层面看,就我有限的观察,哲学社会科学中有很多学科的发展,是离不开翻译的。以哲学学科为例。我看了最近五年的《哲学研究》,把参考文献当作观察点,发现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所列的参考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术译著。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学术译著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和参照,对学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很高兴地看到,前几年,南京大学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工作由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主持,在科学的数据支撑下,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做出了评价,出版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这份报告很明确,中国人文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并不限于中国学者的著作,还包括学术译著,该书主编苏新宁的几点观察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一是“国外学术著作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苏新宁,2011: 10),二是“大量的国外管理理念、国外管理学经典著作对我国管理学初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学者在研究中大量地参考引用国外的著作”(苏新宁,2011: 10);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报告特别强调“国外大量的经典著作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并产生着极大影响。”(苏新宁,2011:11)在苏新宁提出的这几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大”“极大”这样的评价字眼,充分证明了学术译著对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及相关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所起的重要推动力和学术影响力。而学界在引用译著时,对译者的忽视或轻视,就其根本而言,是对翻译的不尊重,和对翻译价值的不认可。
关于翻译之为用的评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学界需要在对翻译价值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翻译的新使命,对翻译如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尤其是进行历史的研究。同时,对社会或学界对翻译之为用的理解偏差或轻视现象,要予以警惕,敢于揭露与批评。
2、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原则与方法问题
当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着两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一是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话语的科学性,二是中国话语的可接受性。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还是外交、政治话语,在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层面,都有不少疑惑需要澄清,也有不少问题需要解答。我们发现,就翻译界而言,对于中国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关注与思考不多,而对中国话语的译介方法讨论不少,有的研究很有启发与价值。但其中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话语的对外译介,考虑更多的是可接受性,似乎只要能够被接受,任何方法都是值得鼓励的。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在国内,官方的或个人的话语不容置疑,少有人提出质疑或批评,而一旦译成外语,这种国内通行的话语很有可能以可接受性、以表达地道的名义,而遭到所谓的变通,有的被修改,有的甚至被替代。比如,在有关中国话语译介与传播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就提出,中国话语多战争隐喻,翻译时需要变通,以任正非的语言为例,认为类似“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表达,如果直接译成英语,军事气息太浓,英语读者难以接受,应该做软化处理,译为“开拓出一条新路来”。又比如,我们国内的一些新概念,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果直译,外媒会不解或者误解,翻译时应该做变通。这些问题如何认识?翻译时应该改还是不改?实际上,任正非是军人出生,他说话向来有军人的风格与气势,面对霸权与压制,他的一些带有战斗气息的话语,是他独特而有意的表达。软化变通,是否合适,值得思考。但是,由任正非的话语表达,我们去聚焦当下的有些话语,战争隐喻确实很多,对此,我们要反思的便是话语本身了。对原文本、源话语而言,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考验,翻译可以反过来促使原文本、源话语进行反思。通过翻译,对拟译的话语可以有新的审视、新的评价,可以为改善源话语起到参照作用。外媒对我们国家或政府提出的一些新观念、新概念、新话语的不解或者误解,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有立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因素起作用,为了外媒的所谓接受,而篡改或变通我们的话语,是否合理,需要商榷,需要探讨。
实际上,认识的不一,也会导致翻译方法和处理方法的不同。不同语种之间,对同一新概念、新术语的翻译,也会出现差异或不同。比如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研究院在2023年初发布的2022年度新词的英文与法文的译法参考,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同一个词语,如“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英文译法为“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而法文的译法则为:“Une nouvelle forme de civilisation humaine”“la sinisation et l’actualisation du marxisme”。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对于原文的理解和处理差别甚大,比如“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语种译文所用的 model与forme, human progress与 civilisation humaine。“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翻译,差异更大,涉及对原文的理解与表达两个重要方面。此处所反映的问题是多层面的:中国话语的关键概念或词语,不同语种的翻译是否需要有统一的原则?对原文的理解是否应该有统一的认识?不同语种对同一关键词语的翻译,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哪种方式更符合我们翻译的目的?
两年前,我注意到“译·世界”微信公众号转引了一篇来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公众号的文章,题目叫《陈明明大使谈如何翻译中国政治概念》。陈明明先生曾任中国驻新西兰、瑞典等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早年任过外交部的翻译室主任,也担任过中国翻译协会的常务副会长,是外交与政治文献翻译的权威专家。据有关报道,他曾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和机构做讲座,就中国政治话语的译介阐明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其中最为重要一点,便是要用地道的英语来译介中国话语,有时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需要调整原文、进行变通。据该文章介绍,陈明明先生提出过两个例子,都是习总书记的话语(原话),很具代表性:一是与习总书记生态价值观相关的著名金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是体现一切为人民的思想的一段表述:“在人民中寻找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这是习总书记在达沃斯主旨演讲中说的一句话。从话语的表达看,可以说兼具严谨的科学性与表达的生动性,思想深刻,语言鲜活。但在翻译中,陈明明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第一句不应该简单地直译为:“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as good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而应该进一步深刻理解并表达“金山银山”的含义,译为:“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这一译法已被中国官方媒体广泛使用,十九大报告英语版也采用了这一译法。但我们注意到,同一个金句,在中国的对外宣传机构也存在多种译法,有的很忠实,采用的是直译,有的则大胆改译,把“绿水青山”也改了,译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原本形象、生动、亲民的表达,变成了抽象的表达,从根本上篡改了原语的表达风格与特征,也失却了原文所指向的亲切易懂的表达诉求。这个例子的翻译,有特别值得思考的地方:形象性的话语,是否有必要译成抽象性的表达?我记得,在2021年12月16日,我参加了国际法语国家组织举办的2021年度五洲文学奖评审会,参加会议的评委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奥巴尔迪纳、法国著名诗人维纳斯·古丽-嘉塔等。会议开始前,我曾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翻译,请教了勒克莱齐奥等作家,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认为直译最佳。由习总书记的形象表达,我想起了毛泽东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翻译。按照时下业界主流的观念或翻译策略,“纸老虎”或许会被抽象化,解释为“吓人的”,或者会采取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或地道的表达,替换为“稻草人”。类似这样的句子或说法的翻译,我们发现几点:一是没有统一的原则,随意性很强;二是从形象化变为抽象化,失却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三是只考虑语言的所谓通顺,忽视了这些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话语特质。这些问题,需要学界进一步思考。
关于第二个例子,据那篇文章说,陈明明先生将之译成“Developmen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我们都知道,这句译文的后半部的句式与表达,出自于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译界一般定译为“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翻译,看似很经典,估计听众听到这样的译文后也会欣然接受,甚至会鼓掌。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习总书记独具风格、逻辑严谨、思想深刻的表达,变成了林肯思想与表达的简单挪用。据那篇文章介绍,说这一译法“国际上反应很强烈,引起了共鸣”①。可细细考量,我们想问:译文受众欢迎的到底是什么?是误以为习总书记对林肯的引用?是认为翻译高超?看似受欢迎的翻译背后,失却的是习总书记思想的深刻性与科学性。更有甚者,有网络跟帖者据此提出荒谬的观点:“中国的发展理念,如果能用西方的核心概念来表达,是一个完美的对接。”对此类观点,我们不能不引起警觉:中国话语的对外译介,有方法问题,更有原则问题。学界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思考与回答:中国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感染力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话语对外译介进行变通的依据是什么?在原文中,中国话语的科学性与表达性如果没有问题,译介中是否需要变通与改变?中国政治、外交话语的概念与独特表达在译介中是否要尽量保存?有否必要以可接受性与语言地道的名义去变通甚至改变中国话语的独特立场与表达风格?
3、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
前不久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翻译专业博士点建设的研讨会上,王东风教授在论及当下的翻译研究时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翻译研究离本体越来越远,少有就语言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与探讨。我很认同王东风教授的这一看法。新时期的翻译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有理论构建与创新,有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多维研究,更有对中国话语译介与国际传播的探索,值得鼓励。但我发现,在当下的翻译研究中,特别是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很不够。
世界的认识、表达与构建,语言不可或缺。换句话说,没有语言,就无法认识世界、表达世界与构建世界。当我们考察翻译、理解翻译时,语言往往是我们需要考量的第一要素。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首先有白话文运动、再次有新文学运动,然后有新文化运动。没有白话文运动,就难以有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我曾指出,在“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是先锋,语言是利器”,着重论述了翻译与语言的紧密关系,认为语言的革新,是文化革新与思想创新的基础,指出“在语言变革与思想启蒙进程中,翻译的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许钧,2019: 2-3)。在《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中,我也曾提出要从文字、文学、文化三个层面去考察翻译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文化的沉淀。文学翻译,从文本的语言出发,由一词一句开始,最后又回归到一词一句。语言,是文学创作关注的基点。莫言写过一篇文章,叫《语言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他明确追求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把他书写的文字打上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风格烙印。阿来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文学翻译,在其形式上,是语言的转换和生成,涉及理解、表达、生成、接受与传播等翻译的全过程。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视野在不断扩大,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研究的方法也极大丰富,但是对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的本体性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传统观念被质疑、批判,变通的翻译策略被追捧。在我看来,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文学翻译的“信”的原则被动摇。《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一文对这一问题有关注,有论述,也有分析(刘云虹、许钧,2014: 6-17)。文中特别提到《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头版“文汇深呼吸”栏目刊登的“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系列报道之七《“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该文第一段便明确指出:“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要更新了!”(刘云虹、许钧,2014: 11)当日的中国新闻网转载了该文,题目为“‘忠于原著’成文学走出去‘绊脚石’”,之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国内主流媒体又转载了中国新闻网的推文(刘云虹、许钧,2014: 11)。翻译研究界对于文学翻译的“信达雅”,有质疑也有批评,有学者就认为“信达雅”这一“三字经”桎梏了我们的翻译。文学翻译中的“信”,大都与语言问题相关。文学翻译要坚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抠字眼”是不能随意否定的。严复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说,这个名,就是词,就是字眼。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推崇的理想翻译,是逐行对照翻译,对原文本的尊重,对纯语言的探寻,都应该以尊重原文的语言表达为出发点。
二是文学翻译以接受为名,对原文的语言表达做随意的变通。翻译界对“信”的质疑与批评,是以破除所谓陈旧的翻译观念为目的的。而破除了“忠实于原文”这一陈旧观念,在我看来,是为翻译主体的变通、删改、甚至连译带编打开了一种通道。语言问题,涉及人类思维的根本。没有语言的革新,不可能有思想的创新;没有语言的突破,也不可能有文学的拓展。诗歌的独特性,首先在于语言的创造性。对于诗人而言,诗是生命的表达,诗人语言所能抵达的深度与广度,便是生命疆域所可能构成的深度与广度。好的诗人,是把生命的体验与言说推向生命未曾抵达的边界。这样的语言,普通的读者一时难以理解,是必然的。这样的语言,给翻译造成障碍,引起抵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对这样的困难与障碍,译者应该在语言的险绝处坚持探索,在目的语中再现出诗人语言的创造性,体现源语表达的特质,还是以读者的接受为名,以目的语所谓地道、通畅和可理解的表达为名,随意加以变通?法国著名文论家、诗歌翻译家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针对翻译界所谓变通的做法,认为自己像诗人策兰(Paul Celan)一样,面对有的翻译,“觉得自己做出的努力尤其促使他抗拒将自己的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因为身为诗人,他总是焦虑地、一字一句地检验自己的语言,因看到它遭践踏、遭戕害,可能还永久地遭到了毁损而痛苦。”(博纳富瓦,2020: 314)策兰的担忧与痛苦,导致了他对翻译的拒绝。作为翻译学者,当我们看到以读者接受为名而对原文随意加以改造、变通时,是否应该意识到这种变通与改造可能践踏的就是原作者的心血,毁损的就是原文的特质?在《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关于翻译与语言的问题》一文中,我曾提出:“面对原作对目的语提出的挑战,翻译者的态度与行为便显示出各种样态,有妥协的,有任意改造的,有归化处理的。但也有接受挑战的,在目的语对原作的抵抗处,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在异的考验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直接抵抗中,探索语言新的可能性,拓展新的表达空间。”(许钧,2019: 5)鲁迅是个范例,他很清醒,自觉地反对随意变通这种翻译方法。他的清醒,在于他认识到翻译应该引进新表达、改造汉语,改造思想。他的自觉,便是他坚定地维护原文的特质,坚决地在抵抗处寻找翻译的可能,拓展思想的疆域。
文学翻译,尤其是中国文学外译,往往强调译语的地道与流畅。对于文学语言,余华有独特的见解。他提醒要警惕文学语言的“普通话”现象。此言意味深长。他所言的“普通话”,是标准化,是大众化,是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如今的文学翻译,是否也有“普通话”现象?值得翻译界警惕。
文章来源:南大翻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