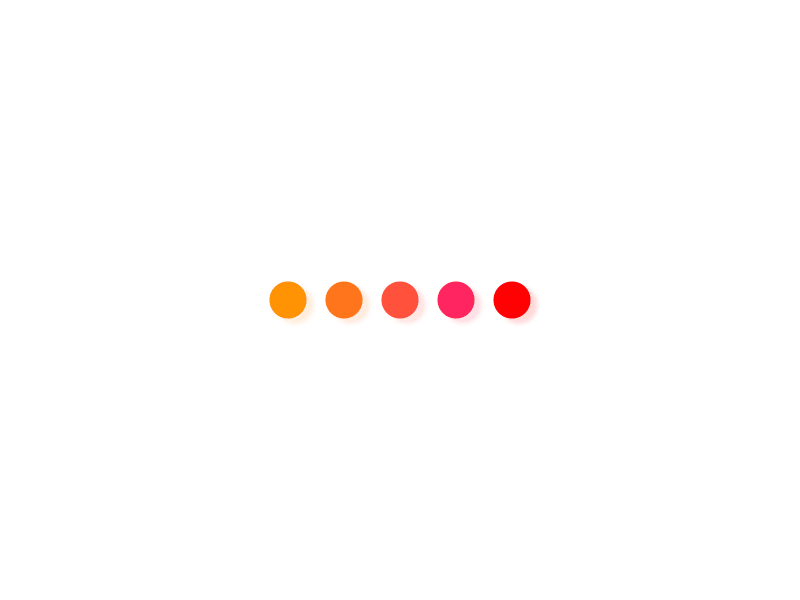zuojiaxinganxian
作者简介
朱羊:原名朱国军,供职于大庆油田井下特种设备修理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成员。作品散见于《小说界》《微型小说选刊》《百花园》《金山》《小说月刊》《天池小小说》《华文小小说》《小小说大世界》《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岁月》《石油文学》《海上文坛》《黄海文学》《当代文学》《精短小说》《微篇小说》《小小说月刊》等报刊杂志。曾出版小说散文集《一杯茶》。
狗兄弟
朱羊
单身狗们的晚饭通常是极早就结束,早得让你以为是一连气吃了两顿午餐。所以,我们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腆起球圆的肚皮散步,这于消化很重要。
我们迎着那轮即将西沉的太阳,徜徉于横穿草原的公路上。那太阳真红,又大且圆,仿佛一枚烂熟的被遗落于草丛中的西红柿,诱人恨不能扑上去咬一口。路边我们种植的杨树的枝叶早已褪尽了绿色,微风徐来,扯几片枯黄的叶片悠悠地飘下,令人蓦然想起是秋季。
“喂,你成哑巴啦?”阿良在我的后背上不轻不重地捅了一下。
对他这喜欢动手动脚的毛病,我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强烈抗议,然而终无成效,他甚至连想纠正此癖的念头都未曾动过。
“喂!想啥呢?”他不依不饶地又捣了我一拳。
我一个趔趄,才不致跌倒。心想跟这种缺乏教养的人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故沉默不语。就在他再次来捶我之际,我霍地跳开。
这时,身旁匆匆走过一位上井的采油女工,阿良就追上去,嘻着脸问人家吃过饭没有,女孩慌得手忙脚乱地紧跑,待展开一段距离之后回敬一句:“有毛病!”
阿良听见了,像白捡了一百块钱一样,高兴得哈哈大笑。
“她是谁?”
“我怎么知道。”阿良瞧见我,脸上的笑纹顿时收敛殆尽。
“奇怪,不认识你跟人搭什么话?”
“呆瓜,你指望人家上赶子喊你吃饭呢?”
对于他的嚣张,我一向是无可奈何。他的蛮横在当地可是家喻户晓的,大人小孩儿没有几个不怕他的,他有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叫疯狗。
我弯下腰去,从枯草丛中揪起一片依旧深绿的草叶,双手夹紧,凑到唇边吹,那声音听上去像公鸡打鸣。不一会儿,草叶吹破了,就重新换一片,这次,又好像小狗在哭。我悻悻地将那片草叶塞进嘴里,学野牛一样,狠狠地将之嚼碎。
“你有毛病啊?”阿良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太阳终于落下,在遥远的天际留下一抹残红,一大片乌云被风驱逐着,缓缓地飘移过去,像为一座涂着红色油漆地板的舞台降下了帷幕。天,就此黯淡下来。
我们的合影摆在靠北墙的那只不久即将落架的大木箱上。照片里有个尖头尖脑的家伙雄赳赳地站在我们中央,那是我们的大青,一条依然流淌着野狼血液的德国牧羊犬。这张照片许是我们屋里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因为它极清晰极充分地证明了别人称我们为“狗兄弟”之言完全不存在诽谤之赚。林丽每次来都会伏在箱子边上看,鬼知道她感兴趣的是我们还是大青?
阿良在练俯卧撑,每晚睡觉前他都练,天长日久成了习惯。因而他的胳膊足有我的小腿肚子那么粗,发达的肱二头肌像一只跃跃欲动的蛤蟆。
我继续读那本《小说创作十戒》,寻思若早两年拜读,也不致走那许多的弯路,抑或如今己成为靠摇笔杆子吃饭的作家了。
我一直想当一名作家,大名鼎鼎的。这个梦从十七岁那年开始做,迄今己逾十度春秋,除却躺在床下的不曾拿出去发表的大作外,还有一抽屉想拿出去发表而编辑大爷们又不屑一顾的稿件。退稿信总是不缺,照例写一些不拟刊用多多联系的字句,我也就当真,厚颜无耻地再写再投。
那只老鼠又准时出现在暖气片底下,棕灰色的毛皮佛如涂了一层油彩,亮光光的,显得格外有精神。我们每周为它预备的两包耗子药,它已提前两天一粒不剩咀嚼干净,居然不死。阿良说这是它命不该绝,还说若是大青仍在,它也不敢来。
我于是黯然,心里对这耗子更加深恶痛绝,但又不敢碰它,无奈,只得眼睁睁地瞅着它的胆量一天天大起来,拖曳着细长的尾巴,神灵活现地沿着墙根溜来溜去,俨然一副这屋子本该就应有它一席之地的架式。
我感到一阵恶心,迫不得已学了一声猫叫,叫得我的嗓子像被谁拿刀剜了块肉般的疼。老鼠自然吓得屁滚尿流地逃了,甚至连我也怀疑在那一瞬间,自己是否真的变成了猫。
天还未透亮,阿良便爬下床掰那约有我脑袋大小的哑铃。凡遇不顺心意的事,他就这样起五更爬半夜地穷折腾,对此我也早已经习惯了。
前几天队上评选上半年度先进个人,他因一票之差而落选。当上先进的人,黑鱼湖温泉游玩一天,单位还管饭。
我晓得这小子是在向我示威,可我一点也不后悔没投他的票。
咚咙……咚咙……咚咙……
“哥们,您关照一下,能否去外面练呢?”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可怜兮兮地哀求他。
“去外面?好啊!”他阴阳怪气地陪着笑。
我不由感到意外的惊讶,这家伙是绝少如此无条件地采纳我的建议的,正值我大惑不解之际,他果然原形毕露,一把掀开我的被子: “兄弟?要去外面练还不走?”
我明白自己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多少日子的实践证明,阿良要我做什么,我最好是知趣地随他的愿。这总比最后他反拧着我的胳膊强行迫从潇洒得多。这个恶棍!心、肝、肺都生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难得起如此大早,冷不丁儿出来,顿觉全身清爽许多。
太阳已经升起,被云遮住,散发着朦胧的微光。一缕缕缥渺的雾气在晨曦缭绕中袅袅向上升腾。
我尽情地呼吸着来自草原的湿漉漉的空气,晨风中弥漫的微微的芳香令人陶醉。我惬意地舒了一个懒腰,一颗心仿佛被那草尖上的点点露珠浸透得马上就要融化了似的。
井房与周围的树木,相隔着一块平展的空地,阿良在空地上不歇地翻着筋斗,这小子上小学的时候,得到过一位游方和尚的指点,学过几手三脚猫的功夫,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和李连杰打上一架,他说要是凭拳脚不能取胜的话,他会考虑用砖头……
林丽是这座井房的主人。
假若没有大青,我们或许永远不会认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叫林丽的姑娘。
大青还未断奶,阿良就从他的哥儿们那里抱来养了。由那天开始,曾立誓不吃早饭的阿良开始早早起床买饭了。大青就是吃我们的大米稀粥长大的。我们尤其喜欢听它用舌尖贪婪地卷舔粥米时发出的沙粒轻敲鼓面般的“啵啵”声。
小家伙生得毛茸茸、胖乎乎的,很是招人怜爱。我向阿良恳请过好几次,央求他将大青的所有权分给我几个晚上。我想搂着这么个可爱的小玩物睡觉一定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殊不知阿良听了我的话,竞如同一位不能容忍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一样,板结着一张狗脸,极尽刻薄地冲我咧嘴道:“你可得了吧,你睡觉太不安生,大青给了你,保不准让你压死呐!”
我很恼火,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本是欲料中的事,令我不能容忍的是,在他的眼里,我居然连一条狗都比不上!
“它是你爹呀!”我难以抑制胸中这股子闷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式。
但闻大青在他的被窝里“嗯、嗯”两声。
阿良这一回却显得出乎寻常的豁达,他向我呲了呲那口比狗屎还灰的牙,心平气和地笑:“随便你讲……看在大青的面子上,估且饶你这次,倘有再犯,我非砸扁你!”
说罢,便酣然睡去。
数天后,阿良终于在我的沉默面前露出妥协的姿态:“兄弟,别为一条小狗伤了咱哥俩的和气……这些天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可把我憋曲坏了。”
“哼,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到底还认得兄弟……”
受降交接仪式特别简单,我匀一条褥子与他交换大青。
翌日,我方晓上了阿良的大当。怪不得他肯将大青出让给我!原来那大青每夜都要于被窝中排泄一些白天未能排泄干净的东西。天哪,我的暄暄的褥子!
为了保障供应大青的给养,阿良几乎天天拽我去饭店,去到人家吃剩的饭桌上拣肉骨头。
有时,阿良在往我撑开的塑料口袋里填塞肉连连的骨头时,常不免咕咕哝哝的:
“这些个吝啬鬼,咋不把骨头也吞下肚?”
“真少见这么馋嘴的人,赶咱家大青了。”
后来,阿良干脆做了一个小铁罐,轮流送往各家饭店,店家慑于他的威名,每次他去取铁罐时,都是装得满满的。即便是这样,他有时也会为了骨头的质量吓唬人家:“还想不想干了,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店老板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忍气吞声将骨头调换了。他们的心里算盘着,宁可生意亏点儿,也总比惹上这条疯狗好得多。
瞧着大青活蹦乱跳的样子,阿良兴奋得手舞足蹈,还拼命捶打我的肩背,有力的震撼令我的心口隐隐作痛。
我有些恼怒,又不敢与他动手,只好狠狠踢了大青一脚,大青一个七百二十度滚翻,呜呜地叫个不停,委屈地蜷作一团。
阿良惶惑地上前将大青搂在怀里,急得两眼通红。
“你蹄子痒了去石头上尥去!大青招惹你啦?大青咋招惹你啦?”
我揉搓着依然酸痛的肩膀,气昂昂地与他俩对视着,又憋不住笑疼了下巴。
大青见我怒气消了,蓦地挣开阿良的拥抱,摇晃着尾巴颠颠地朝我跑来。
大青直立起两只粗壮的后腿,呜咽着,两只前爪错落有序地上下揖动,它这是在向我赔礼呢,我不禁茫然,大青究竟何错之有?
望着大青虔诚的眼睛,我的心底不由泛起一波酸涩的愧疚。我扭转身子避开它的注视,我不愿让大青看见自己掉眼泪。
“知道不?打狗还得看主人呢……”阿良兀自喋喋不休。
大青在身后“噢噢”地凄叫着,一会奔跃至我的身前,一会又喘息着窜回阿良的身边。
阿良越说越气,捋胳膊挽袖子地冲过来,看见他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的心底也禁不住有些发毛了。
“大青!你还为那他求情?“阿良冲着紧咬他裤角不放的大青咆哮道。
“唔……唔……晤……”大青迷茫地沉吟着。
事后有一段时间,阿良的确不敢轻易与我动手动脚了,我清楚他是怕大青吃亏。
某日午后,一个女孩面对大青友好的问候,居然吓得声嘶力竭得尖叫起来,那叫声将大青吓得仓皇逃走。
大青迅疾地扑回正在油井房旁纳凉的我们中间,显得极度的恐惧,它依偎到阿良怀里方才无忌地低吟起来,纤细的腰脊不停地轻微地颤抖着。
“谁他妈吞了豹子胆啦?”阿良呼地跳起,似一头狂怒的不可遏制的狮子吼道:“小子,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我抚摸着大青滑软的身躯,小心翼翼地将它眼角处的一粒草籽轻轻地吹落掉。
“它,它咬人!”女孩子不知于何处胆怯地应了一句。
阿良用食指在鼻尖下来回划了划,又喊道:“胡说!我们大青从来不咬人的!”
那女孩由一面墙后边挪出半截身子,她的样子真是狼狈透顶,满头乌发蓬乱,一张黝黑的脸孔汗迹斑斑,再经那沾着新鲜油污的工作服一抹,活脱脱一位非洲土著。
阿良看得有趣,口气随之缓和了许多:“喂,说话可得凭良心啊,我们大青真地咬你了?”
“它……它抢我的样桶!”女孩抗议加声讨。
大青有了依靠,冲那女孩子突然暴吠一声,吓得女孩又缩回到墙后去。
“怎么样?我们大青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良慢条斯理地说着。“我说:“老妹呀,别以为我们是畜生就可以任意诬谄,那是要犯错误的!”
“别以为我们大青是畜生!”我不得不及时纠正他犯的关键性语病。
“是它抢我的样桶,你们……“女孩在墙那边气鼓鼓地争辩。
我似有所悟,我想大青一定是误将她提的样桶当成它的装肉骨头的铁罐了。除此之外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大青,去把东西送还人家!”我命令道。
大青一个激灵,略略迟疑了一下,旋即似一条黑色的闪电没入密匝匝的草丛中。倏忽间,一只漂亮的镀锌油样桶被大青叼出来……
“啊呀,别叫它过来,啊呀,救命啊!”女孩儿终于放弃了所有的矜持,向我们求救了。
“喊啥?我们大青是给你还桶呢。”阿良开心地大笑。
“啊呀,快让它站下!”女孩慌恐地再次惊叫,然后,竟出人意料地一个箭步跨出墙外,在草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逃着。
阿良双手抱肩,紧咬着牙,直眉立眼地注视着面前这一切。
我实在看不过眼,高声将大青吆唤回来。
阿良扭头忿忿地斜了我一眼,揶揄道:“真他妈的扫兴?咋的?对这位小妹妹有点儿想法?”
我没有理他,提起样桶,一言不发朝那姑娘走去。
她拂顺散乱在额前的长发,嗫嚅着说:“那人是叫阿良吗?”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微笑了一下。心想,这个臭名昭著的阿良呀,简直到了天下无人不识的地步了!
“怨不得那么坏呢?”女孩嗔怒地啐了一口,胸口由于惊怒,剧烈地起伏着。
“其实他这人还不错。”我将油样桶递进她黝黑而纤长的手中。
女孩慌慌地掠了我一眼,不胜感激地莞尔一笑。
女孩接过桶,又朝那边的阿良与大青投去恨恨地一瞥。
“谢谢你!”她柔声说道。
我如坠九重云雾中,浑身如同遭遇电击一样,麻酥酥的。
女孩转身时,一缕淡淡的薄荷香水味从她那柔软的微微散动开的发隙间飘荡出来,我木然地伫立在原地,怔怔地望着她的身影渐渐离去,愈来愈远。
“老妹,不送哟。“阿良流里流气地喊。
“汪、汪、汪……”大青欢快地轻吠着。
然后,整片草原重又落入无边的宁寂之中。
后来,阿良再与那女孩见面时总会有几番唇枪舌战,那女孩自然少了先时的畏惧。时间长了,彼此也就熟了,女孩透露名叫林丽,是刚调到这里的采油工,还说自己来此之前,就听说这地方有个坏得冒浓的阿良。
阿良居然为她那句话着实难过了好长一阵子。
传达室有我的信。
信封被里面的东西撑得鼓鼓的,不用说又是退稿。我沮丧地抓起信揣进口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如何摆脱那浓浓的惆帐,无数次的挫败将我编织的未来之梦残酷地扼杀于襁褓之中。
临出门时,有人于暗影处嘻嘻地窃笑,那令人心悸的笑声使我想起那只仍滞留于我们房里现今以磨食砖块为生的硕鼠。我的五脏六腑恰似被谁用铁掀深掘了一锹,一阵令我痛不欲生的痉孪如乍起的飓风将我席卷于地。舌根处仿佛坠悬着一块巨石,使我欲呕不能,感觉自己就象一帆在海中触礁的小船,逐渐朝海底沉落……
我恍惚地睁开迷蒙的双眼,看见数重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飞快地旋转着,旋转着。渐渐地,那重影慢慢明晰了,原来是阿良与大青立于床侧。
“哎呀,好歹活过来啦!”阿良揉着红肿而鼓胀的眼皮,“都他妈三天了,愁死老子了,我打算你今天再不醒就往火葬场挂电话……。”
大青乖觉地移近至我的床前,喉咙里呃呃有声,它轻卷着精薄的舌尖舔舐着我的胳膊。倾刻间酥麻传遍了整条臂膀。我任由它表达这独具特色的安慰。
我有些累,撤回了手,掌心里托着大青眼中默默淌落的泪珠,我在心里小心翼翼地品味着那咸腥苦涩的滋味。
门开了,一道炫目的光束刺得我两眼生痛。没有看清楚来人,但我分明感受到那淡淡的似曾熟悉的气息。
“林丽!”我好不容易想起来。我想这么喊一声她的名字,郑重其事地在她面前喊一声她的名字。然而,我的嗓子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燥涩哽塞得发不出声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那被一层桔红色工装遮掩的亭亭身躯,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
林丽径直向我走过来,轻盈地坐在我的床边,从衣袋内扯出一块手帕,轻轻地为我拭去脸上的泪迹。
阿良诡谲地冲我吐了一下舌头,默默地牵着大青出去了。
“你的病……阿良都告诉我了,你真是犯傻……其实,我不像你想得那么好,更不值得为我……去……我来……就是想告诉弥,我们都应很好地活着……”
听着她的话,我蒙了!这该死的阿良!
我机械地摇着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阿良这人真讲义气……大青可懂事了,每天去公路上接我上井……有它跟着我什么都不怕……”林丽继续轻柔地说着。
生活,就像那沉睡了多年神秘莫测的大草原,永远有令我们捉摸不透的内容。谁也无法道清这其中的渊源,因为可知的生活实质上是不存在的,正因为生活无时无刻都在呈现那朦胧的魅力,这世界才变得精彩十足,才更加有意义。
林丽再来过几回,我竟然大病全愈!
“怎么样?我早料到你害的是相思病,我那林妹妹一来,你好得蛮快嘛……”阿良在最唇一次喂我红糖姜汁时,不无得意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哑口无言,不知道是否应该感谢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大青终于出落成一条壮犬。哈着一条血红的长舌片,双耳像两面小旗似地朝天竖立,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宛若两孔深不可测的寒森森的水潭,一声威吼,通体的毛发,刹时间针立如刺,那条挺直的长尾拖迤于两股之间,狼一样的雄健,真可谓是凛凛八面威风,不可一世。
黄昏里,它抖擞一身黑黄相间的油晃晃的毛皮,纵跃于草野之中,惊起无数鸟雀凄呜着向天扑去。在草原的土路上,它经常引来路人羡慕、惊恐的目光,令我们也体验到一种极透彻的自豪。
距此十里之地,竟有一人慕大青之名不期而至。那人便是养鱼暴发户陈麻子。
他亲眼目睹大青的威仪后,口口声声连赞“好狗”。并许诺说想办法为大青谋个户口,条件是让大青去帮他看守养鱼池。
阿良没容他讲完当即一口回绝。
陈麻子无奈地绷紧那张肥硕的凸凹不平的面孔,掏出现金三千元,硬往阿良的手里塞。阿良用力一扬手,钞票飞得满天飘。
“你会后悔的。“陈麻子撂下话,悻悻地走了。
一日,大青竞神出鬼没般叼回一只活生生的肥鸡来,喜得阿良与大青抱至一处滚作一团,我不免担心日后会因此生出事非来,劝阿良将鸡放了,再给大青一次最严厉的警告。然而阿良却乐不可支地一个劲儿夸赞大青劳苦功高。
“你若想洁身自好,可以不吃嘛。”阿良说。
如果,我的意志再坚强一些的话,如果,我们的伙食能够再好一些的话,我一定会坚持让阿良送还那只鸡的。然而,我终于还是妥协了。
我相信谁也想象不出那只鸡的味道鲜美到什么程度!因为做鸡是阿良的绝活。这是当年他偷过许多人家的鸡之后,苦练而成的绝活儿,我饱饮了两大碗鲜美至极的鸡汤后怡然睡去。
醒转之话,听林丽说她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么香的鸡肉。她还说阿良给大青一只鸡腿作为犒赏,大青却没有吃,叼到我的床头,而后就趴在地上用舌头卷吞涎水……
我的心头一热,再看空空如也的床头,问那鸡腿怎么不翼而飞了?林丽说,是阿良一时吃性大发,就风扫残云了。我不免对此饕餮之徒嗤之以鼻,再找大青,也不见踪影。
后来,附近家属区陆续发生家禽失踪的事。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骂声四起。有的邻里之间,甚至为互相猜疑而大动干戈,我们隔岸观火,故意装聋作哑。同时也为大青的聪明能干而庆幸。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大青终于还是出事了。
林丽亲眼看见大青被人用猎枪打倒在公路上,然后急忙跑来报信了。大青是去公路上接林丽上井时被那群有备而来的人打倒的。
待我们发疯般赶至出事地点时,竟连大青的尸体也没能看见。
公路边,残留着一滩污血,黏稠稠的。阿良凝视着尚未干透的血迹,瞠直了眼,他缓缓蹲下身去,茫然地摘拾着粘在血泊中的大青身上掉落的茸毛。
我们望穿双眼,期盼大青能够神奇般地出现在面前,然而大青依旧是音讯杳无,我们终日游荡于草野里,公路上,居民区内,无力地呼唤着大青的名字。
大青的遗毫被葬在井房边的那棵最粗的大杨树下。
入土的时候,阿良特地买了两只鸡,炖得香烂烂的,一并埋掉。
阿良蹲坐在坟前,一脸的懊丧。他用小刀在自己的左腕上木讷地雕划着大青的名字。殷红的鲜血随着锋锐的刃尖的蠕动淋漓流下,滴落于他膝下的粘黄的土地上。
“阿良,想开些吧,你不能这样作践自已啊!”我竭力阻止着他的毫无理智的举动。
阿良两眼冥冥地漠视着我,两星瞳仁里没有一丝光泽。他一句话也不说,牙齿残忍地错动如月下反刍的牛。两腮青筋绽露如同扭成一团的蚯蚓,我捏手捏脚从他手里将刀子夺下,他浑然不觉,旁若无人地抓起一把坟上的稀松的浮土,紧紧地将伤口敷盖住。
林丽从草原上采撷来好大一捧野花插满大青的坟头。而后,便倚着树,轻轻地哼唱着,歌声中充溢着无尽的凄凉与忧怨,那歌是极熟悉的: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
时光飞逝,不觉间仲秋临近。队里提早为每人分了十块月饼和一箱易拉罐饮料。这在从前是绝无仪有的,因此大家都很高兴,有些离家近的人便搭着便车回家去团圆了。
我被留下值班,塑着一辆辆汽车从平坦的柏油路上疾驰而过,卷起纷纭的尘埃在团团黑蓝的浓烟里坠下,感觉到一种从不曾有的失落。我知道阿良此时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他最不喜欢过节了。
阿良几乎忘记了他曾有个家。
阿良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他因为没有哭而被爸爸打得满屁股流血。其实,他当时很想哭,只是害怕躺着的妈妈听见他哭会突然醒来。慢慢地,阿良一天天地长大。就模仿他爸爸打他的样子去同别的孩子打架。他觉得打人蛮有乐趣,甚至想过有朝一日像他父亲打他那样去打他的父亲。然而,这个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就进了少年管教所。
一年之后,他从那里出来。一心想扑到来接他回家的爸爸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是爸爸根本没来接他,阿良后来知道父亲不来是为了另一个女人。从那时起,他就怨恨起自己的父亲,更厌恶那个女人,直盼到参加工作,便身如离笼之鸟,再也不愿回家去见他们……
阿良盘腿坐在床的一端,静静地吸着烟,娴熟地朝屋顶吐出一串串高质里的烟圈儿,他的手腕上的刀口已结成凸起的大青字样的疤痕,那是一段属于我们的永恒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床中央摆了几瓶启开盖子的罐头,一把不锈钢勺深深插嵌在那只滚圆墨绿的西瓜之中。
我觉得胸口有些气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后勉强笑道:“怎么?今天过节不喝酒?”
阿良用小指勾开一听易拉罐,轻轻呷了一口,淡淡地说:“戒了。”
“为什么?”我接过他手中的饮料,仰头喝了个痛快。
“不为什么。”他悠悠地说,凝视着腕上的字迹,许久也未动一动,呆板得像一尊塑像。
我们谁也没有胃口,对着邵些东西发了一阵呆,就互相望着对方。阿良挟了块午餐肉送至我的嘴前,我张口去咬,他却极快地将肉送进自己口里吞了。我觉得这一招儿好是幽默,便笑起来。他也跟着我一齐笑,我俩终于笑出了眼泪,好似两个吃饱的傻瓜。
“我们唱首歌助助兴怎么样?”阿良建议道。
于是我们就唱,扯开嗓门尽情地干嚎,我们差不多什么歌都会诌两句,这主要是受林丽的影响……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唱的时候,阿良冷丁儿冒出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没有唱,我觉得那歌好悲壮。
“想家吗?”我问。
他一愣,眼波中漾溢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郁,他激动地望了我一会儿,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紧咬着两腮,努力不使自己落泪。
阿良一拳将怀里的西瓜捣碎,沙哑着嗓子说:“来,吃一块,过节了,咱们也他妈的高兴一回,这西瓜还是林丽犒劳咱们的呢。”
“林丽?她可好久没有来了。”
“她下午打过电话来,说是分到别的区了。”
“她没留下什么话吗?”
“她把咱们的照片拿去了……她说永远忘不了我们……”
“单单是这些?”我不禁茫然无措道。
“她是哭着走的……”
……
我们走出屋外,迎风而立。
夜幕笼罩下的草原,被一处处忽明忽暗的灯火点缀得分外饶丽,那闪射着光辉的地方隐约传来的机器的轰响,伴着声声蛐鸣合奏出一首美妙婉约的草原小夜曲。
夜色里,有几只小虫嗡嗡地乱飞,时而没头没脑地碰击我们的面颊。我琢磨这也许是一种别致的问候,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举头望那无垠璀灿的满天星河,不免疑惑道:“咦?你看,今晚没有月亮!”
“大概是被天狗吃了吧。”
“哦……”
广袤深沉的草原深处,不晓是甚么声音悠悠地低吟……
大青?
难怪今夜没有月亮!
3、参赛稿件必须是原创首发,在任何媒体和微信平台发表过的作品禁止参赛,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
本刊主编:谭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