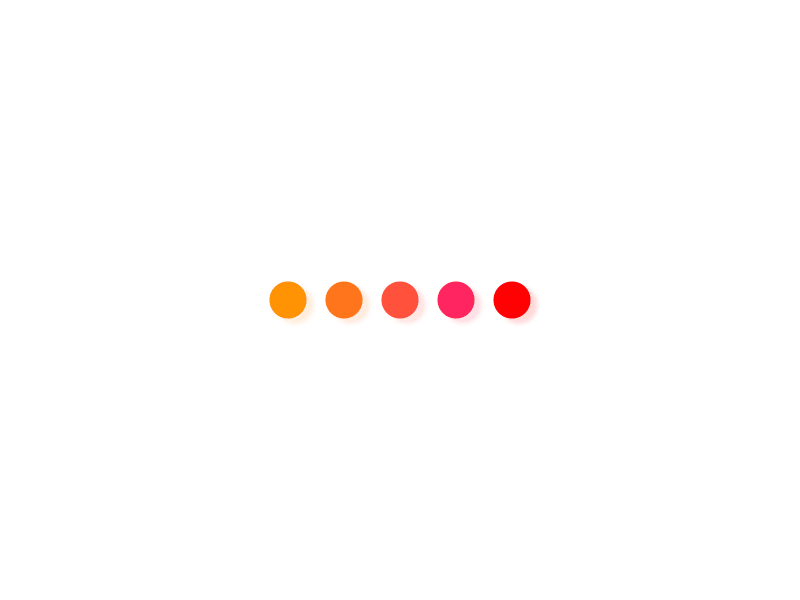世界上没有哪个孩子不爱雪糕的吧?
即使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我的童年,也能见到雪糕的影子。
那时,买得起冰箱的人家不多,小卖铺也没有冰柜卖雪糕。
装开水的保温瓶,被毛巾裹得严实的泡沫盒里,藏着那种吃起来只有糖味的冰棍,如果你用力一吸,原本染了色的冰棍可就变成白秃秃的冰碴子啦。
我小时候,要从抽屉里找来找去,才翻到被妈妈遗忘的一分两分钱,攒一段时间,挑一根冰棍。
要吃到加了奶油和牛奶的“高级”雪糕,得到一个叫做“冰室”的地方。
我们县城只有一家国营冰室,开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所有的小孩都知道那个地方。我妈妈就在那里上班。
一到晚上,冰室大马力的吊扇就吹得呼呼响,铺了瓷砖的地面,被冰室的阿姨们拖了一遍又一遍。站在门外,就觉得全身凉透了。一到周末,那里全是带小孩来吃冰的家长们。
有时我悄悄从门口路过,看见妈妈系着白围裙,把头发盘在白帽子里,低头在大玻璃门后干活。
她原来坐在办公室记账,春天穿雪纺的连衣裙,冬天要把蕾丝手套摘下来,再轻轻地拨算盘。
那时我常过去玩,办公室的叔叔阿姨也喜欢给我一些小本子画画。不知道是从哪年夏天,妈妈就开始在冰室上班了。
有一个卖雪糕的妈妈,我太高兴了。
同学的妈妈在新华书店上班,我们都猜,是不是能看世界上所有的书;有一个当老师的妈妈,会不会知道所有作业的答案。大家都羡慕我,有一个在冰室上班的妈妈,我想吃多少雪糕就有多少雪糕。
可是妈妈,不让我去冰室,她说雪糕吃多了,对牙齿不好。
我只能悄悄假装路过。
有一次,我被妈妈的同事看到了,她叫我进去坐着。
我拿到了一个戴棕色小礼帽的娃娃头雪糕。娃娃头一直朝我微笑,妈妈从玻璃门后面走了出来,也冲我笑。她的羞涩感染了我,我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着,让乳白色的牛奶汁流到手上。
又吃了一个彩色冰淇淋球。我第一次看到冰淇淋装在过家家那样的小碗里,还送了一把指头大的塑料小勺。
等一盘点缀着葡萄干和花生碎的冰沙端上来,这场盛宴才到了最绚丽的时刻。
妈妈忙了一会儿才过来,说:“吃太多了,回去肚子要痛。”
“没得事,”招待我的阿姨们把我围起来,“难得来一趟嘛。”她们问我,在哪所学校上学,又读的几年级。
过了没多久,私人冷饮铺也渐渐增加了一两家,冰室还在开着,去的人却越来越少,妈妈也从那里调到了一家国营饭馆。
饭馆晚上接待酒席,白天卖米粉和包子。我们家饭桌上常常有妈妈从酒席上打包的剩菜。她为了干活方便,也剪掉了长发,在忙碌的身影中,我总是找不到她在哪里。
有时候放学经过,妈妈会大声喊住我:“等等,我给你装两个包子。”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起那顿盛宴,从此再也没品尝过像那样甜蜜的雪糕,等我也到了妈妈那时候的年纪,这种回味,才渐渐泛起一丝苦涩来。
“卖雪糕的店开门了。”孩子们之间悄悄传递着一个消息。
早在三月,柳树刚抽条那会儿,紫荆花的花骨朵还没像往后那样鼓起来,卖雪糕的店就拉起了一道门缝。在不下雨的清晨,老板走出来,拿一把秋天芒草扎的扫帚,扫了扫门前的台阶。
孩子们上学经过,惊奇地发现这一幕,大约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的心里就像藏了一只土拨鼠,这里钻一个洞,那里鼓起一个包,上课也坐不住。
捱到放学,跑过去一看,果真,原先那些堆成山一样高的柚子,都不见了,原来卖柚子的胖阿姨,也不见了。
孩子们不懂,为什么雪糕店一到冬天就开始卖柚子,原来那些没卖完的雪糕都去了哪里。妈妈们只是一袋又一袋地往家里搬柚子,还说什么,等过年柚子吃完了,老板才能回来卖雪糕。
现在可好,终于不卖柚子了,老板连冰柜也摆了出来,还是那些,方方正正,横三排,竖三排,个个都装着了不得的宝物。
赶快吃罢晚饭,女儿求我带她去店里。她围着冰柜转来转去,眼花缭乱,简直无从下手,全都没尝过,全都想吃。
绕着冰柜巡视个三四圈,顺时针一圈,逆时针一圈,最后再浏览个几道。如果不是大人们一直催着快点快点,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天,细细地看,又竖起耳朵,听旁人说哪款好吃。
店里特意为孩子们装了结实的小板凳,这样年纪小的孩子也能站上去,俯下身慢慢挑选。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没见过、也没品尝过的雪糕呢?每一款都想带回家试试,又怕肚子装不下,妈妈说,牙齿也受不了啊。
趴在冰柜上的女儿,像最严谨的科学家,也像最认真的鉴赏师,欣赏着一件件举世珍宝。
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雪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