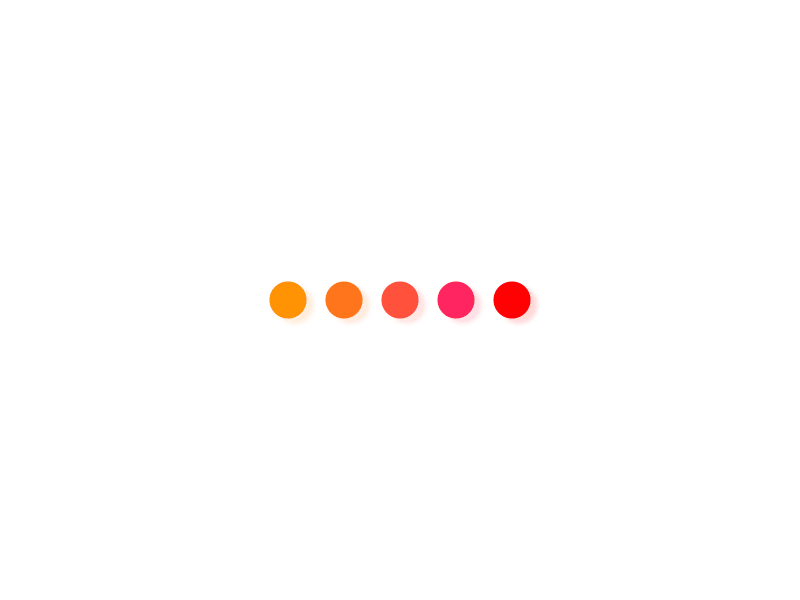在凤台沟里这个特殊的亲戚家,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是在茹古家里奶奶的热炕上睡着,铺着厚厚的褥子,盖着暖和的花被子。可就这我还是冷得浑身发抖,奶奶抱来了一床特厚的被子,压到了我的被子上,又把我推到了最热的炕头上。身上盖得太厚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可我仍然冷得发抖。
奶奶摸了摸我的头和后背,说是感冒了,发高烧身上就冷。她惊慌失措地当起了“赤脚医生”,倒了半碗酒,用火柴把酒点着了,红蓝相间的火苗熊熊地冒了老高。奶奶伸出右手的指头,勇敢地浸到烧着大火的碗里,抓了一下,连酒带火地在我头上、前后心、脚心、手心到处擦了个遍,还用一个不知是什么朝代的小麻钱刮呀刮,直刮出了很多紫点子。接着,奶奶就拿出了那个放过腐酱的火罐,点了一块纸团扔进火罐里,扣到我的后背上。这一扣,可能是火苗烧着了我的肌肉,生疼生疼的,一下就把我给疼醒了。
醒来,我还在发抖,脚疼得厉害,我坐了起来,把脚抽回来摸了一下,像冰块似的。我用手捂住脚,妈妈也伸过手来,捂到了我的脚上。她好像记起了什么,用手在我的腿上摸了一下。我还穿着湿袜子、湿棉裤,她心疼地说:“怪不得你说冷,全是湿的。你快坐到墙角,把里边的衬裤换下来。”说着她就从白色包袱里取裤子,我坚持不换,怕前边的人看见了笑话。
妈妈把被子往我腿上拉了一下,我看清了妹妹是睡在她腿上的,身上盖着被子,难怪她不冷。同时,我也看清了这个说是窑的地方实际是个不大的洞,我们是睡在没有任何东西的地上,很潮湿,虽然身上搭着被子,大冷天还是避不了寒。
外边还是一片漆黑,梅英妈在做饭。他们点着一盏用蓖麻子做的小油灯,在墙缝里插着,照得这个小屋亮了许多。饭做好了,一家四口呼噜呼噜地吃得很香。
趁天还黑,妈妈叫起了妹妹,要带我们出去解手。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往出爬,妹妹5岁,看见我们爬着出去她也跟着爬。在外边墙角的杂草中解罢手,我们就赶紧回“家”,以免路人看见。
妈妈没有做饭,初来乍到什么也摸不着,她从布袋里掏出冻得硬巴巴的窝窝头,我和妹妹各拿了一块儿使劲地啃着,咬一口就出来一个白茬子。这时我想起来了,昨天妈妈提的布袋里边装的就是窝窝头。
多亏提来了它,虽然难啃但也充了饥,肚子没挨饿。
天渐渐亮了,我看清了和我们一块住着的那四个人。个子最高的是太仙家,他对妈妈说:“咱们是邻村,你娘家在连村,你家里老人我认识。”他很友善,说话和气,慢条斯里的。听了他的话,妈妈也附和了几句。在这儿人和人之间都是压低着声音说话,倒像小偷似的,不敢理直气壮地大着声儿说话。
梅英爸坐在最前边,面朝洞口,阴沉着脸,没有吭气,显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我和妹妹都怕他,不敢正视他。
梅英妈说话也是慢悠悠的。梅英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有一张还算好看的脸,惹人喜欢。她说她18岁,比我大10岁。
妈妈对我和妹妹说:“你们叫他们俩人都是伯伯。”(指俩男的)我想爸爸和妈妈是同岁,妈妈27岁,他们一定是伯伯。妈妈要我们叫梅英妈姨姨,梅英当然就是姐姐了。
吃了饭,坐着没事干,又不能多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聊地熬着漫长的日子。可耐的时间长了,大人们也低声说说话儿。
梅英妈问妈妈:“你为什么事儿,带着两个小不点儿跑到这里来?”
妈妈说:“姐姐家在秀岩村,她的小叔子(贺兆峰)结婚,我带孩子参加完婚礼,姐姐一家留我多住几天,就没有走。昨天,茹古有人来秀岩办事儿,说我们家被‘封了门’,姐姐要我们躲上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就把我们送来这里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明白了我们为什么来了这儿。
妈妈问:“咱们什么时候能做饭?”
梅英妈说:“早晨不等天亮就得做饭,晚上外边全黑下来才能再做,两头都要摸黑,还要操心不能让过路人看见冒烟,一露馅,咱们就束手就擒了。”
梅英妈还告诉我们:解手得快去快回,不能站到外边,不敢说话,也不敢笑。
梅英爸一直没有开过口,梅英妈说完了话,他突然从前边爬了过来,抓起妹妹的手,阴沉着脸说:“就你小,不准哭,哭得让走路的听见了,就来把你抓走了,再也见不到你妈妈了!”
妹妹抬起头,瞪大眼睛瞅着他,她的小手一直捏在他那大手里,吓得想哭。梅英爸拉下脸,厉声说:“不准哭!”妹妹用一双泪眼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个陌生人,没敢哭出声来。
妈妈抚摸着她的头。梅英爸放开了妹妹的手。妹妹一下子钻到了妈妈的怀里,再也没敢转过头来看一眼。
梅英爸的话,道出了他闷闷不乐的原因,他是担心我们的出现会对他们带来后患,担心小孩的哭声会引来抓人的人。后来,妈妈提起这件事儿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家是没有错的,说什么话都不过分。担心是正常的,不能怪他,也没有理由怪他。跑的目的就是怕被抓住,如果被抓住,不就前功尽弃了。”
妈妈做饭是用梅英家的钢盔锅,也叫日本人“帽子”。一天做两次饭,他们家做完饭,吃完了,妈妈才做。
趁着伸手不见五指时,妈妈在外边拾了一些干柴棒,锅是搭在洞口旁,用大土块垫起的炉子。妈妈做了一锅小米焖饭,她先喂妹妹吃,我自己端着吃,姨姨给我们带了两个碗,两双筷子。有时我和妹妹就把饭吃得只剩锅巴了,剩多少妈妈就吃多少,妈妈吃饱了没有?我们不管,只顾自己。再要吃饭,要熬到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时,妈妈饿吗?有什么可以充饥的吗?开始还有那干窝窝头,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
又是一天早晨,姨夫乘天黑又送来了小米和窝窝,还有蓖麻子,要我们像梅英家一样,自己做灯照亮。姨夫走了,妈妈说:“窝窝没有放的地方,就先吃了它。”可是,刚吃下不久,妹妹就说肚子疼,妈妈给她揉肚子,我抓住她的小手,摇来晃去地哄她。她哭了,抽回了我抓着的那只手,捂到了自己的肚子上。妈妈尽力地哄着,不让她哭出声来。可她越哭声音越大,头上冒出了汗,哄她不行,打又不忍,妈妈急得头上大汗淋漓,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的人也都急了,这样哭下去眼看就要出事儿,你看我,我瞅你,太仙的伯伯没有说话,脸却涨得通红。梅英妈一直哄着,梅英盯住看没有说话。我在妹妹的脸上摸来摸去,急得火烧火撩的。妈妈哭了,我也哭了。
梅英爸忍无可忍了,他大喝一声:“再哭就滚远点,狼就等着吃哭的孩子哩!”可妹妹不管说什么,还是哭个不停,捂着肚子来回打滚。妈妈一点儿办法没有了,只见她突然转过身去,从后边抽出了那个“白包袱皮”,在手里很麻利地拧了两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妹妹的鼻子和嘴,死死地揪着这块布的两个头。妹妹渐渐哭不出来了,眼睛瞪得圆圆的,脚在不停地蹬着……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声嘶力竭地大声哭,拉着妈妈的手使劲搬,梅英妈也急忙过来帮忙掰妈妈的手。妈妈松了手,我不哭了,妹妹也不哭了。
妈妈紧紧地把妹妹搂在怀里,她的脸贴着她的脸,眼泪簌簌地掉到了妹妹的脸上。我坐在她跟前一直憨憨地看。
妹妹瘫软地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惊醒过来,睁眼看看妈妈,就又睡了过去。
这件事儿过去没几天,太仙家的伯伯对妈妈说:“我们想转个地方,这儿人多,地方太小,你看是和我们一块走,还是……”
妈妈明白了,于是,她没加思索地说:“哪儿也不去了,你们走了我就带她们慢慢地往回转。我一个人带上两个孩子,没吃没喝的,跑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终究要跑个什么呢?”
听了妈妈的话我高兴极了。洞中住了二十多天,好像几年似的,我实在憋不住了。
太仙家说:“那也行,你们也慢慢走吧。从前面那条坡上去就到了垣头,上了垣路就好走了。沟里路不好走,也不安全,既然是往回走,也不怕见人了。”
妈妈说:“不怕见人,离秀岩近,我们先去那儿。”
太仙家说:“我给你指个地方,孩子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那里歇歇脚。上坡后往东走不太远的地方,地塄下有一孔烂窑,是放牛、放羊的避雨的地方,对着的村子就是凤台。你们就慢慢地走吧。”
梅英一家人在这里吃了最后一顿饭,饭后就准备启程了。
妈妈趁人家的锅也做了最后的一次小米焖饭。这次饭做得多,妈妈把吃剩下的焖饭和留下的一个窝窝装到了一块儿,妈妈说路上吃。
平时做一次饭,我和妹妹几乎要吃光,这次却剩下了。我明白了,妈妈是不舍得吃,她饿着肚子让我们吃饱。
我当上了妈妈以后,体会到了妈妈疼爱孩子的心,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的。想到妈妈那时饥肠碌碌的忍耐,我的心绞痛着,我真没有勇气去想象她当时饿着肚子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