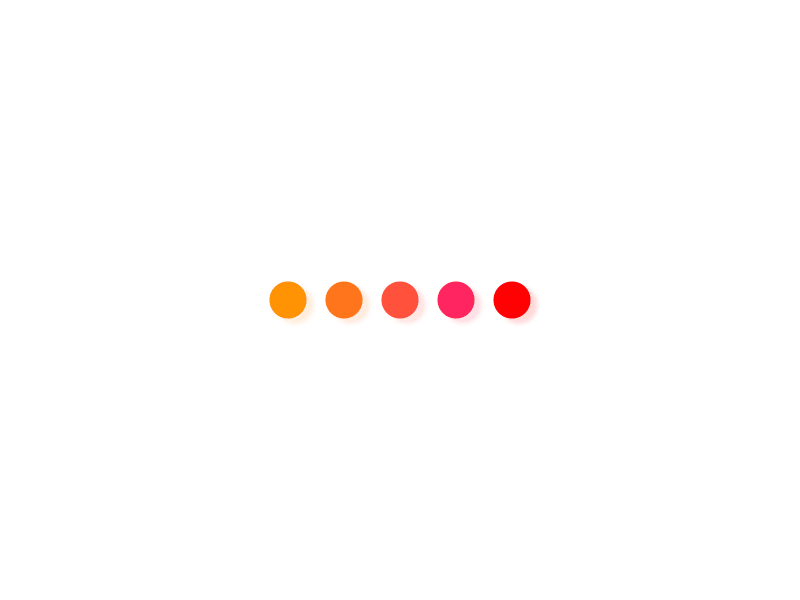2008年,我做了自己的在线工作室,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用来养活自己。确实也想过走私毒品以及贩运军火,可惜没有摸到可靠的门路。2010年回国后,11年在北京宋庄租了个院子,就这样到了2014年,那一年,我休息了一整年什么正事儿也没办,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大呆,或者整个下午都在除草,人跟草斗,也没什么乐趣可言。
2014年春天到2015年夏天,想起来就是一片烂糊糊,连记忆本身都模糊不清,我只记得草从低到高,秋天的晚期如其枯萎,整个冬天我都不在状态,回了老家陪伴母亲,勉为其难地翻译了几首拉金的诗,然后等着开春,看自己能不能随着春暖花开打起精神来。
那段时间,我已经开始写作为私家侦探的以千计小说系列,推理小说,完成了几个短篇,分别是《消失在折叠空间的村长君》,《她那么美》,《兴趣小组》和《有人迷醉于天蝎的心》,自2011年以后,一年一个短篇的节奏。写得特别地慢,也特别地谨慎,生活就像个骗子,我不再追求产量,好小说每个句子每个词都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实验在写作班上学到的那点儿精华,明白了一些道理。
起了头,就不要再有烂尾楼,没有写不完的短篇,乃至于中长篇,这是我最新的认识,也许是低迷期更加有利于明辨是非,那些我过去以为是秘密的东西,一点点浮现于表面。重新去读曾经读过的小说,也发现了那些写得好的小说家,一定是早已经发现了这些隐秘的规则,小说是可以学习的,基本功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初学者如果不肯下笨功夫,则永远会在飘忽不定之中稀里糊涂地写下去,最终只有放弃一条路。
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
15年夏天,我打算把原先的工作室做个改版,做成现如今的宿写作中心。
简单说,无非是教诗歌和小说,还有一点儿非虚构文章。
因为一下子千头万绪,不知道先开什么课,我就喊了几个原先跟我学习笔记分析的学生,记得有八个人,开了第一期的读书写作课,他们稀里糊涂地上了课,又不敢报警说上当了,每节课我介绍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的一本书,第一节课布置个写作的作业,下周的后半截课程就挑选写得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的,出来说。我上课从来没有什么温婉可人的语气,他们也都敢怒不敢言,很多学生连夜扔掉了书架上的很多畅销书,怕下一节被我抽查,冷嘲热讽他读书的品味不行。
乱棍之下,必有后福,这八个人很快养成了买正确的文学书的好习惯,成了宿最早一批会读书的人,同年11月,我请了小说家阿丁来讲小说课,我自己在次年春季开了第二期的读书写作课,到了秋天是第三期。学生们开始写诗,写小说,也是这一年。
我们是个线上的写作中心,小班课程开头用QQ语音群,后来转移到了微信群。然后我请了吕约讲诗歌课,第一年就我们三人,我们还组团去单向街做了一次我的新书《瓶中人》的活动,在一起嬉笑怒骂没个正形儿。教人写作,先得是个真实的人。
我说服吕约的方法很简单,说,我就是想要做个西南联大中文系,当年联大中文系,好教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自不必提,唐云钱钟书都在期间,最爱逃课的学生都成了汪曾祺。西南联大的校长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联营,大家以不管具体事儿为核心,联大有一种自由的气氛,教授们讲的东西各行其是,自己能自圆其说就行,就连讲课的风格都难以拿语言来形容。我就想要宿是这个样子的,过程中不管怎么样,封闭的写作中心之后,出口出来了一批诗人小说家,各有各的样貌和形状,谁也不像谁,也不像他们的老师们,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
自做宿写作中心以来,我就觉得什么事都很容易,我们的课程基本上都要收钱的,除了阿丁的小说课,六周一千二之外,大部分课程六周都是八九百,都在学生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也有免费的微信大群,一个月请一个诗人,小说家或者出版人讲一次课,第一期讲了半年,讲课的是:盛兴,恶鸟,王小妮,李修文,王泡小泡,也挺受欢迎的。
我发现盛兴讲课不错,请他加入微课计划,微课计划是个一整年的课,有24节,请七八个老师来讲,贾葭讲非虚构,沈浩波讲诗歌,周云蓬讲读书,盛兴也讲诗歌,张柠讲小说,我和阿丁以及吕约还是各司其职。
学生们开始在群里贴诗,有几个已经写得又凶又好了,诸如慢慢(她的男体笔名是我起的,叫做箱邦久),偷摸在朋友圈写了一年,被我偶然发现了,也许就是发现慢慢已经写得出了很好的诗歌了,让我有了信心去激发更多的学生写诗。恰逢此时,沈浩波开始上微课计划,他非常善于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总是鼓励他们去写,去贴。我们又做了公号,有了晚安诗这样的名目,大家都以写诗为荣耀,感觉宿这个乌托邦就是用来写诗,写小说,别无他用的,大家发了诗,还会有人发红包跟赞赏,干别的未必得到那么多鼓励。
一时间,同学群里,涌动着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梅冬陈,盐渍乌贼,mohan,宋肠肠,黑瞳,君君,紫气,yoyo,三洛,简天平,远镜,多多,忍者神,何止,潼喜喜,wf,胡之….都是一些一出手便有了自己的风格和方向的家伙。写诗难吗?我总觉得不太难,但是一直写就难了。
以下,我将大张旗鼓地介绍介绍他们,大部分是她们。
实际上,多多和陈三是读书写作课里面写得最好的两个。多多天性敏感至极,我以为她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一定相当师奶,见到真人,好像少女一般,我在深圳短期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起去做一些非常女性化的事情,买高跟鞋,做指甲,跑到专柜让人给我免费化妆,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更漂亮。她做事认真,而且拖沓,一定要拿着小钉锤叮嘱她,但结局总是好的,她有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我也听了一部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不写诗简直天理难容,可是她的产量跟我的期待总是反比,这大概是个叛逆期的少妇吧。
不想说陈三了,写了大概一首半就退出诗坛了,他学测绘的,有一阵子想做无人机的飞手,想想而已,并不会真的去做。
慢慢非常有趣,异性缘跟同性缘一样好,她热情当中带着一点儿冷酷,而且聪明绝顶,跟慢慢聊天乐趣无穷,她总是能够把任何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下,在课上,她是唯一敢技巧地调戏和顶撞男老师的女学生,而且多数男老师也乐意被她调戏和顶撞。所以,她一直是班长,在任何时代,慢慢这种人在各种复杂恶劣的环境下,活下去的机率都是很高的,不单是领导保她,群众也会张开温暖的怀抱抚慰她。何况,她的诗写得实在是又多又好,总是有一段时间,看到她在写诗,不管谈不谈恋爱都多少能写点儿,欣慰。

梅冬陈是图书编辑出身,射手女,她最早在我的小院儿实体课上出现,坐在那里就跟个女诗人没什么区别,我说:你不用学了,回去随便写写就行。又一周,她开始给我们看她写的诗,像模像样,不负众望。又过了一周,我布置写个小说,她写了《上射阳》,将自己小时候跟父亲们去射阳城里,穿着大棉裤尿裤子的故事,代入感太强了,读完那个小说,我很长时间总是忍不住摸摸屁股,总觉得那里凉飕飕的。她嫁人前夕,想买一件白色的衣服婚礼上穿,试的都是两三百的衣服,果然是山东女孩儿,质朴无华,笑起来跟傻子一样,写起诗完全没有底线,像一个北欧女性。我试图跟她做朋友,但是她不同意,她挺高冷的。
后来,她告诉我,射阳不在山东在江苏。女孩儿,我只喜欢山东的。
mohan是清华大学学生物的女博士,会的东西特别多,她的朋友圈我差不多都看不懂,一会儿讲编程,一会儿讲天体物理,一会儿又打算练习个什么大提琴,智商过剩到可以滴滴,如果普通人的智商是一碟咸菜,mohan的一定可以供应整个朝阳区大妈整个冬季的咸菜所需。她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依我看,是害怕当众说话,智商会外泄,而我跟她短暂见过的时间,仿佛也被智商的火花溅到了一些,回家后,居然就找到了丢失许久的钥匙。
盐渍乌贼常年在西藏工作,是个学ngo的学生,和藏羚羊一样,她很少下到平地上来,我们也无缘跟她接触,她写的诗跟陈丹青早年的画一样,是西藏题材的,但是显然比陈丹青的画儿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气象开阔极了。
宋肠肠别的事迹我知之甚少,有一次师生人肉见面会之后,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她小声跟我讲了一句连男人都很难讲出来的情话,鉴于这句话是我们之间的隐私,即便是写文章也不可以出卖朋友的。这样的话,唯有诗人才好意思讲。
潼喜喜我倒是经常见的,她总是随叫随到,只要说:“我在天黑以后咖啡馆”,她大概一个小时后就会从城里赶来,然后我们就在天黑以后咖啡馆一起瞎哼哼,那里有一支麦克风,老板做的咖啡很好喝,老板娘很白,这是我和潼喜喜约见的圣地。白羊座的她写起诗来有一种狠劲儿,还特别会读诗,公号晚安诗的音频版,她的铁粉最多,临睡前听一听她读的诗,可能会再也睡不着了,起床后也写不出诗来,特别适合不上班的无所事事的人群。潼喜喜干别的行不行我不太知道,她很会索吻,我每次分别的时候都会亲她一下,至于亲哪里,得看她那天好不好看,要命的是,她每天都很漂亮,真是讨厌缪斯,女神一定玩忽职守了,才会让一个写诗的人那么经得起观看的考验。
黑瞳原本叫做王小草,她的志向是做个小说家,但我总觉得她好像应该多写诗,然后再去做个小说家。君君的志向也是做个小说家,我觉得她确实可以直接做个小说家,顺道写写诗。
忍者神是个配音导演,她潜伏了好长时间才开始写诗,开头的时候,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到处找人开小窗打听怎么写诗,我也被她深夜打听过,当时快睡着了,被请教这么大问题非常烦躁,一句话打发了,果然,她再也没有来找我打听过了,她找到了更好的老师,过了一段时间,写出了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倍的诗。
至于yoyo,俗称yo姐,是跟我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我们差不多跟结婚了的人们一样和谐共处,最近我去上海上个课,住在她家,我们整天两人瘫在沙发的两头读书,我老眼昏花,她家的吊灯昏暗极了,我看一行字就会睡着,而她压根不会睡着,她只在该睡觉的时间睡觉,这种与我互补的特性促使我常常做什么都喊她一起。她的主业是个it女,感觉跟机器有关的,跟app有关的,跟社会运转的系统有关的,她都明白,她教会我去东航办了拖了二十年的会员卡。
“yo姐,请问,什么叫做银行流水?我为什么要去银行打流水?”深夜,忍者神跟我打听怎么写诗我不想回答的时间,我在问yo姐更重要的事情。
“说了你也不明白。”她说,“我帮你远程打吧,哪家银行?”
“银行都有哪些?”
“嗯,以你的能力,最多有工行的。”
她简直是活人里的侦探,而且我只有一张工行的卡,偶然去一次日本,都要找她借信用卡,她在国内接到银行短信,bibi,您卡上消费了26000元,bibi,您卡上消费了42000元。yo姐很高兴,觉得我终于学会了花超过一百块钱的钱。
写完yo姐,我感觉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以下说一说公号编辑部。
早先就写得很好的Alastor成了宿写作中心公号的A主编,茶曦是我从免费课程群召来的公号小编,她也写诗,慢慢和多多加入后,我封给她们两个副主编的头衔儿,反正头衔很多,不怕多给。有一阵子我封官加爵习惯了,遇到一个人比较顺眼,就会问他:“你想到我们哪儿做总编嘛?我们还有ceo没找到人选。”
利用这两个承诺,我和yo姐免费喝了很多酸梅汤和王老吉。
有了公号就跟有了自己的杂志一样,我们又开设了不同的栏目,诸如专门做人物非虚构采写的“人物宿写”,mohan写了盛兴,多多写了诗人莫渡,都费了很多力气,后来小儿写了宿的诗人、水下摄影师三洛,写得又轻松又浪漫,不久前,君君写了早年的先锋女诗人伊蕾,伊蕾本来是我的偶像,她的《单身女人的房间》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读了,惊艳又称奇。有一天,宋庄的朋友陈鱼带我去她家,原来她家离我家不到五百米。又过了些日子,我们竟常常走动,她喜欢花儿,我常常摘院子里的野花家花给她,她都喜欢,还吃过她做的饭,也是很俄罗斯很好吃的。
宿的学生们本质上不是学生,就是一些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些人生历练的人,很像当年文革后的77、78届大学生,都是一些被生活洗过好多次热水澡冷水澡的人,甚至也有不少六零后七零后的人妻们,狮多是其中一个,主职是河南一家银行的高管,我挺惊讶于写诗时的自信跟不拘的,有女王的气度,她的笔名也是我给起的,我起笔名特别便宜,一百块一位,挣到的钱就到公号编辑部给大家发红包,如此,大概也发了两三千块的红包。所以,宿的不少诗人都是我起的笔名,有些人学会了起笔名,自己起,但也带着一点儿我起的风格,很有意思。
我意识到,生活中出现一些可以随时虐的学生还挺不错的,我常常到群里挑拨离间,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互相仇恨,没有一次不大获全胜,总是有人上当,事后,我又总是追悔莫及,受到良心深重的谴责。自写诗以来,跟各种诗人保持着不太亲密的距离,这群崭新的诗人是我一手造成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搞一场集体婚礼,有几个女生已经打算去台湾结婚,并结伴养老。我想在云南租一块山里的地,也许做个特别小的营地,夜里有一盏灯,够照亮读诗的人即可。宿给了我一个做梦的更大的理由,沉溺于白日梦,并采嫩补老。
当然了,我们在生活中也见面,诸如到各城市做书店活动,就去聚一聚,见到活体,我们叫做,又称师生人肉见面会,我至今没有品尝过师生恋的滋味,也是很可惜的,希望其他老师特别是男老师们,有这个福分,女老师要跟学生谈恋爱,且谈成一个法国总统,在别的领域也许可能,文学上是绝无可能的,想从政还来写诗干嘛?不如直接一点儿。
很奇怪的是,好像自从有了宿写作中心,我就再也没有长时间地自闭,不高兴跟郁郁寡欢,一下子做了那么多人的母亲,整天换尿布跟喂奶,大概也没时间发愁了。我的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只要坐下来,总能够打出来几个字,托这些永远年轻的年轻人的福。
这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乌托邦,目前只有两岁,但我觉得余生可待,可以一直有,也不枉我当年,隆冬之间,哈佛广场喝了那么多杯外卖的咖啡,吃了那么多难吃的甜甜圈。
可是上帝,我是去上小说课的,世上有多少人能够专门去上小说课的?

插图/Ryan McGinley
编辑/Alastor
除了写作课,我们什么也不干
你就没有回头路了